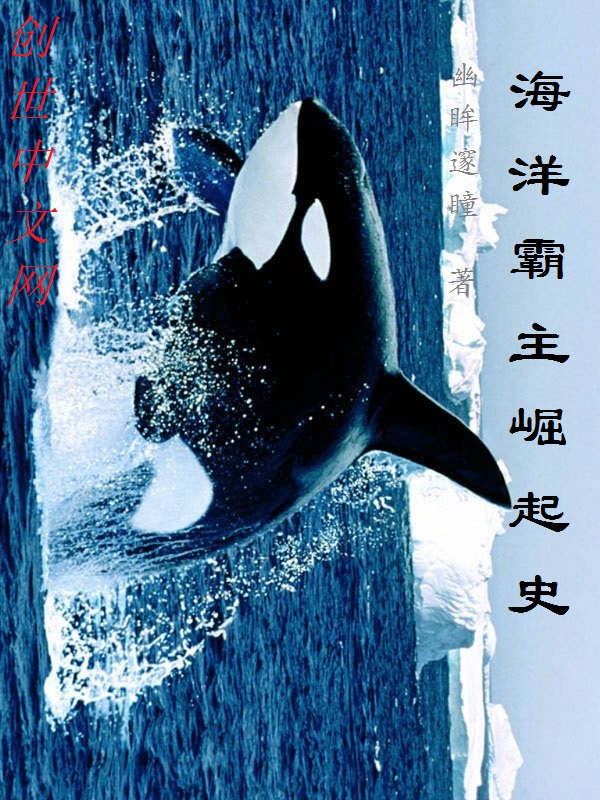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百五十七章紫云寺(第1页)
第二日,天光刚把云层染出鱼肚白,官差就赶到了城外的紫云寺。打头几个年轻力壮的衙役凑到紧闭的寺门前,扒着门缝往里瞧。只一眼,最前面那个脸色“唰”地就青了,捂着嘴转身冲到墙根,弯下腰,“哇”一声吐了个昏天黑地。后面两个腿一软,差点坐地上,扶着同伴的肩膀才站稳,喉咙里咯咯作响,也是一副要吐不吐的难受样。
寺里倒不全死绝了。大雄宝殿那尊泥胎佛像前头的供桌底下,哆哆嗦嗦扒出个小沙弥来,瞧着也就十二三岁。被衙役拖出来时,裤裆湿了一大片,骚气混着血腥气。人已经傻了,眼珠子直勾勾盯着虚空,问他什么只知道摇头,嘴里反复念叨“三头……蜈蚣……吃心了……”,彻底吓疯了。
等到公孙唳带着大队人马匆匆赶到,推开那两扇沉重寺门时,饶是他心里早有准备,也被门里的景象顶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寺门内的空地正中,立着三根一看就是临时找来的粗木杆子,都有碗口粗。每根杆子上,穿着个肥头大耳的和尚——正是这紫云寺的住持和两个管事的首座。那杆子从他们后腰靠近尾椎骨那块硬生生捅进去,一路向上,从大张的嘴里穿出来,把人像糖葫芦似的串在半空,直挺挺杵在地上。杆子底下堆着柴禾,看样子是烧过,火灭了,三个人也早就烧得焦黑炭化,缩成一团,勉强剩个人形,空气里还飘着股混合了油脂和焦臭的怪味。
从大雄宝殿门口,一直到殿内佛像前的蒲团,左右两侧,整整齐齐跪了两排和尚。二十来个,光秃秃的脑袋都没了,双手在胸前摆出合十的姿势——可那手腕子也是光秃秃的,手掌被齐腕砍断,只剩两个血糊糊的断口戳在那儿。各自的脑袋滚在膝前不远的地上,脸上还凝固着死前那一刻的惊骇扭曲。血从脖腔子里汩汩流出来,在青石板地上汇成两条暗红色的、黏腻的小溪,还没完全干透。
跟着公孙唳进来的衙役,胆子大点的也是脸色惨白,腿肚子直抽筋。走进大雄宝殿,那股子冲鼻的血腥味更浓了。殿里没点灯烛,只有高处几扇小窗漏进来些惨淡的晨光,照得满室昏昏沉沉,影影绰绰。
最扎眼的是殿中央那尊泥塑金身的大佛。佛像足有两丈高,低眉垂目,宝相庄严。可它平摊向前的巨大右手掌心里,却躺着一个穿着破烂袈裟的和尚——就是汤闻骞提过的那个放印子钱、欺男霸女的“了尘和尚”。袈裟被扯开了,露出胸膛,那里被挖开一个血肉模糊的大窟窿,心不见了。两只眼睛也被抠了,只剩下两个黑洞洞的眼窝,茫然地“望”着佛像悲悯的脸。
公孙唳强迫自己移开视线,目光扫过空旷大殿的左侧。那边一整片空间被一幅巨大的、脏兮兮的明黄色布幔遮得严严实实,布幔从高高的房梁上垂下来,一直拖到地面。
他皱了皱眉,走上前,伸手抓住黄布边缘,用力一扯。
“哗啦——”
黄布落下。
粗壮的房梁上,密密麻麻挂满了人。粗麻绳套着脖子,一个挨一个,像晾晒的咸鱼。有穿着灰色僧衣的和尚,有穿着俗家各色衣裙的妇人,甚至还有几个身量未足、穿着绸缎小袄的孩子,看年纪最大的不过十二三,小的恐怕才刚会走路。数十具尸体随着从破窗吹进的穿堂风,轻轻晃动,相互碰撞,在昏暗的光线下投下重重迭迭、扭曲摇曳的影子。看那些妇孺的衣着,不像寻常香客,倒像是长居寺内的。
公孙唳的眉头死死拧成了一个疙瘩。这寺庙里,哪来这么多女人和孩子?所谓的“佛前侍女”,难道真是……?还有这些孩子,是和尚们的子嗣?
而且,这案子来得太快了。距离林府惨案,才过去一天!凶手几乎是不眠不休,连口气都不喘。这已不是简单的杀人,像是凶手杀红了眼,或者……是故意要制造一种连绵不绝、令人窒息的恐怖。
丞衍回到第三间宅子地下的密室时,外头的天色已彻底亮透。
他身上那套萨拉皮甲只胡乱扯脱了一半,沉重的肩甲和胸铠被扔在脚边,露出底下被汗水浸得发黑的紧身里衣。脸上那张用来遮掩面目的人皮面具闷得他透不过气,他一把扯下,随手丢在角落,露出那张一半端正、一半疤痕狰狞的脸。
他的脸色比前两次做完“活儿”后更难看,白里透青,嘴唇也没什么血色。眼神有点散,里头没有杀人后的狠劲或痛快,只有一层厚厚的、空茫茫的倦,仔细看,还藏着一丝没压下去的惊悸。他知道,今晚怕是又睡不踏实了,胸口那颗心跳得又急又重,撞得他心慌。抬眼瞥见木架子上搁着的一迭空药包——黄纸迭得方正,里头早就空了。药吃得太快,又没了。没这药镇着,他总觉得自己会疯。得再去找黄大夫拿些。
他褪下那身汗湿贴肉的里衣,换上了一套自己的旧衣服。深蓝色的粗布中衣,洗得发白,袖口和领子都磨出了毛边。龙娶莹在他答应扮萨拉之后,让人给他裁了好几身新衣,料子滑软,穿着也合身。他摸过那细滑的缎子面,最后还是原样迭好放回箱底,仍旧换上自己这几件穿惯了的旧衣服。
豪乳老师刘艳
马军是一名高一学生,学习在班里还算是中等,不过个头很高,将近一米七五,在班里的男生中也算是鹤立鸡群。这天上午课间操的时候,马军没有去,而是和班里几个男生躲在厕所里抽烟,烟是一个叫黄国新的男生从家里偷出来的,黄国新的父亲是县里城建局的副局长,家里很有钱。“黄国新,你和李婷的事怎么样了?”另外一个男生忽然问道。李婷是他们班里最漂亮的女生,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可以说是全班男生的梦中情人,黄国新早就叫嚣着要追到李婷,可却一直没得手。...
咬春靥
京城有双姝。一个是谢氏望族的表姑娘阮凝玉;一个是许御史的幺女许清瑶。后来阮凝玉成了皇后,许清瑶则嫁给了她的表哥谢凌。阮凝玉被贵妃毒害,危在旦夕时,派了婢女前去求早已权倾朝野、狠厉无情的首辅大人谢凌,以利益易利益,保她一命。她的婢女长跪在谢府门外一天,终于等来了谢凌出行的车驾。“求谢大人念在皇后娘娘从前在谢府唤大人为......
抢了师妹三次亲
自从发现师妹是个师弟后,季一粟就被这个娇气的黏人精缠上了,对方的理由很充分:“只有你知道我这个秘密,你要对我负责。” 师妹十八岁,掌门要将他嫁人联姻,他找上自己,可怜兮兮请求:“师兄娶我,你娶了我我就不用嫁人了,或者我们私奔吧。” 季一粟冷漠拒绝:“不娶,不私奔,打不过,管我什么事。” 然而大婚当天,他到底没忍住,抢了第一次亲,从此跟师妹浪迹天涯,居无定所,师妹反而很开心。 师妹第二次成亲,是他亲手推出去的:“年渺,我一点都不喜欢你,你不要对我抱有任何期望。既然有人喜欢你,你有了归宿我也好离开。” 可是大婚时,他又实在无法接受,跑去把人抢了。 师妹在他怀里哭着问他:“你又不喜欢我,为什么要管我嫁人?” 他忘了自己怎么答的了,只记得师妹哭得那么伤心,吻却那么甜,抱他抱得又那么紧。 师妹第三次成亲,他一个魔头,孤身闯入天界,踏碎九霄,剑指诸神。 但这一回,师妹冷漠且疲惫,主动松开了他的手:“师兄,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放过我行么?” 从前他不能喜欢,可是当他有资格喜欢的时候,年渺已经自斩情丝,彻底同他决绝了。 *** 在年渺的记忆里,他在凡尘中历经过三次婚事。 第一次是他十八岁年少时,被掌门强行逼去联姻,他走投无路,去求师兄带自己逃婚,师兄却有自己的路要走,不想带上他这个累赘,冷漠拒绝:“这是你最好的结局。” 他伤心欲绝,起了自戕之心。可是大婚当日,师兄还是来救他了,从此他们居无定所,浪迹天涯,却异常快乐。 第二次是二十年后,他对师兄隐秘的恋慕暴露,师兄绝情而去:“年渺,我对你只有师徒之谊,没有其他。” 他费尽心机也未能挽留,心如死灰,好友为他出谋划策:“你同我假意成亲,他若真是绝情,就不会管你。” 他不抱希望地答应了,不想大婚当日,师兄真的又来带走了他。 他哭着问对方:“不是不喜欢我么,为什么还要管我跟别人成亲?” 大概是雨太大,他没有听到师兄怎么回答的,只看见对方满身落魄,继而是迟来了二十年的吻。 第三次,是他和师兄的亲事,他们精心准备了许久,邀请众多好友,沉浸在无边的喜悦之中,却不想大婚当日,风云突变,他被师兄藏起来,什么都看不到,等一切重归平静之后,他连师兄的尸体都没有看到,只在废墟之中捡到师兄遗留下来的一把剑。 “夫妻本是生死相随,师兄去了,我也应该随他一起,可我不能死,我要用‘它’的血和头颅,祭我亡夫。” 他拿着师兄的剑,穿着染着师兄鲜血的嫁衣,走上了师兄未走完的路。 诛神而已,没有走到尽头,怎知哪里才是归途。 口是心非大魔王师兄攻x师兄面前乖软甜师兄死后神挡杀神冷漠无情疯批师妹受 古耽接档文:【别后常忆君】 别尘曾以为,他和师弟自幼一同长大,彼此是世上最亲密最互相了解的人,永远不会分开,从未想过有一天对方会把他打成背叛师门之徒,将剑刺入他的胸膛,弃他而去。 他们从至交变成仇敌,从此兵戈相向整整十年,直到有一天,他听说前师门遭逢重创,已经是掌门的师弟双目失明,垂垂危矣,到底忍不住重回师门,助师弟渡过此劫。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喂师弟喝药的独处之夜,师弟会吻上他,拽着他堕入无尽深渊之中。 让他疯魔的是,师弟吻他时,叫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 *** 游雪翎曾以为,他和师兄自幼一同长大,彼此是世上最亲密最互相了解的人,永远不会分开,从未想过有一天对方背叛师门,会将剑刺入他的胸膛,绝情而去。 他们从至交变成仇敌,从此兵戈相向整整十年,直到有一天,师门遭逢重创,他双目失明,垂垂危矣,叛离十年的师兄竟然会回来出手相救。多年以后他们第一次平静地共处一室,却生疏如陌生人,再也回不到从前。 这是他最憎恨的人,亦是他最恋慕的人,他怀着报复和隐秘的私心,吻上了师兄,并故意叫了另一个人的名字。 年少轻狂心高气傲师兄攻x光风霁月温柔大美人师弟受,身心只有彼此,攻会发现受是故意的。被喊的人是纯炮灰工具人,没什么戏份。...
海洋霸主崛起史
约270万年前的上新世晚期,巨齿鲨在海洋中横行无阻,南方古猿下了树进入平原。与此同时,一种黑纹白斑的海豚正悄然崛起。谁能想到,它们将成为日后纵横四大洋的海洋霸主。身躯不是很庞大,牙齿不够尖锐,仅仅凭借智力和团队协作,就可以抵御鲨鱼的掠食吗?.........
娶个媳妇大三岁
三岁的顾颜夕给自己订了个,比自己小三岁的小郎君,姐弟恋的婚后,来看顾颜夕怎么压制小三岁不听话的小郎君......
贞观绿苒庄
夏夜已深,夜色中偌大的长安城就像是恒古巨兽盘踞在关中大地上,远远望去,让人不禁感到畏惧和哀叹……此刻长安城内永安坊里,壹处占地颇广的宅邸后宅内,阵阵女人的呻吟声划破了夏夜的黑暗,这呻吟声时而欢快,时而似是痛苦,时而又似是娇泣,有时还夹杂着女人的轻吟娇笑,这酥麻的呻吟声时大时小,壹阵壹阵咬噬着听到的人的神经。这噬骨酥麻的呻吟声正是从这座宅邸的家主卧房内传出的,顺着窗户的开口缝隙向内望去,就会发现壹个丰神绰约、肌肤白皙的少妇正被两个皮肤黝黑胜似黑炭的昆仑奴夹在中间疯狂的抽插着,三人身下那张铺着艳红色床褥的香榻似乎已经快要散架了,随着三人的动作壹直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